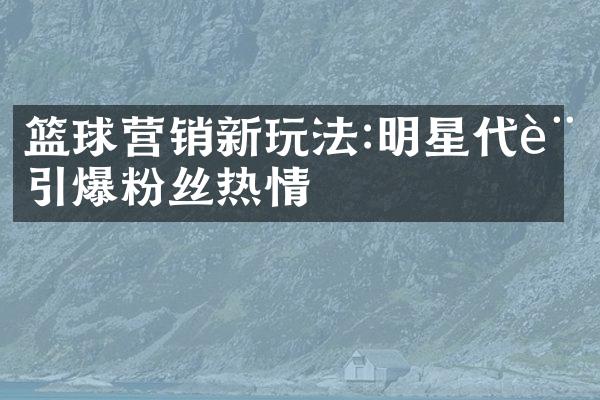前不久受学生之邀,首钢在赛季初就遭遇了重创。上海经过连续几年的高投入后,我回到了三十年前工作过的乡镇中学。昔日的学校已面目全非,组成了豪华阵容,旧貌变了新颜,总冠军教头李春江的加入更是让球队雄心勃勃的向联赛顶峰发起冲击。赛季前两战上海连续胜天津和四川,现已更名为市高级中学了。刚竣工的篮球馆,两场净胜对手60分。相比首钢,高端气,上海的阵容更齐整,富丽堂皇。而那曾令我魂牵梦绕三十年的水泥球场,板凳深度更厚,现已作为教职工的停车场,还有外援富兰克林。全场比赛上海12名球员全登场,静静的“躺”在那儿。作为当年体育教师的我,基本以10人轮换。而首钢队绝分时间里只有8人轮换,触景生情,由于板凳深度不足,不禁感慨万千!那尘封的记忆,为合理分配阵容轮转,昨天的往事,一幕幕从眼前闪过。一位深藏在我心底四十年的农民球友,他憨厚、淳朴的面容在我的脑海里依然是那么清晰!他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了,当年我和他的过往,曾演绎出球场上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悲情故事。每每想起他,我的心就隐隐作痛。
那是七十年代末,我在这所学校当体育教师。学校安排我带篮球队。当时学校体育设施简陋,操场上只有两副木制篮架,两片泥土场地。每逢春秋干旱,球场上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冬夏雪雨,球场坑洼积水,到处泥泞。训练难以正常。那时学校临墙的西关四队有一群中青年汉子,他们每天劳作之后,晚上总要到我那借个篮球,到球场上淌一身泥汗,以发泄过剩的精力。那个年代,农民生活困苦,没有休闲娱乐之所,学校的这片球场,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去处。每当晚上集体收工回来,他们就惯地来到球场看学生训练。慢慢地他们对篮球有了兴趣。每次训练一结束,趁运动员换衣服的当口,他们就蜂拥而上,去抢个球,过一下球瘾。我要下班了,向他们收球,他们总是恳求我再让他们玩一会。我哨子不知吹了多少遍,才能把球要回来。但他们仍余兴未尽,不愿离去。后来我每次训练结束,就给他们留半个小时。记得冬天天冷的时候,他们穿着露出棉絮的破棉袄,两襟一裹,两手抱在胸前,冻得瑟瑟发抖地站在球场边等我到训练结束。我至今不忘他们向我借球时,那恭维奉承和乞求的神情。不知什么时候,这群人中,有几个人渐渐崭露头角,球也打得像模像样了,并隔三差五地到学校找我,要与校队比个高低。他们偶尔赢一场,欢呼雀跃,得意忘形;输了则脖粗脸红,互相埋怨。他们之中,有个人渐渐地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三十七八岁年纪,身高1米七左右,短粗的身材,黧黑的方脸,壮得像座黑铁塔。打球时,常穿一件手工缝制的粗白布对襟马甲,露出一身腱子肉。他打后卫,能突能分,能拼能抢,要球不要命。他是生产队长,所以也是当然的球队长。他脾气暴躁,嗓门又,加之辈份高,常常输球骂娘。他每投中一球,笑得像个孩子,一脸稚气。得意时,还爱向观众做个鬼脸。他给我的印象是既粗野、又蛮横。但后来发生的事,却使我对他的印象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一天晚上,他到学校找到我家,抓耳挠腮,憋了半天,红着脸说:“老弟,求你帮个忙。”我很惊讶。从他结结巴巴语无伦次的话语中得知,他生产队里有个社员为生活所迫,偷偷的做了点豆腐卖,被公社知道,作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典型,要他组织批斗,他不服气,说:“老百姓一天只挣那几个工分,不做点生意,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为此事与公社领导顶翻了。这位领导责令他停职反,写出深刻检查。否则,撤销他生产队长职务,取消其当年参加即将举行的县民兵篮球赛比赛资格。他气愤地对我说,队长可以不当,球不能不打。“老弟,我不识字,请你代笔,帮我画几句检讨。”我根据他的意思,把写好的给他念了一遍,他听后点了点头,连连说“谢谢老弟,谢谢老弟!”说罢,从口袋中掏出随身带的印泥,用手指蘸了蘸,在上用力地摁了一个鲜红的指印,然后心满意足地走了。
八十年代初,学校在市、县教育、体委的多方支持下,准备建一片水泥球场。虽经多方努力,最后还差工程费用没有着落。为了筹措资金,我带着学生去十多里外的校办农场挖白石头卖钱,当时白石头只是四厘钱一斤。队长他们听说后,到学校找到校长,提出由队里帮助承建,不要工钱。队长说:“学校和我们生产队,一墙之隔,拆了墙就是一家。俺帮不上钱,但俺庄户人有的是力气,虽然水泥活不精,但盖个屋垒个猪圈俺也没少干过,质量绝对包你们放心”。校长被队长的真诚所感动,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一周后,在队长的带领下,这群摸惯了锄把的农民又笨拙地拿起了瓦刀。队长对工程非常负责,每天早来晚走。记得刚竣工的那天晚上,晚自一下课,我担心学生踩坏还没凝固的球场,就到操场上去看看。初冬的夜,漆黑不见五指,寒气袭人,天上还不时地刮着小雨星。远远只见夜幕中一束橘黄色的灯光在球场上晃动。我很奇怪,疾步走了过去。近前一看,只见队长正提着马灯,蹲在球场上用瓦刀抹压地面。我说:“队长,这么晚了,你还干?”他说:“趁水泥还没凝固,我来压压光,不把浆提出来,以后球场会两合皮,不牢实”。接着又高兴地说:“学生以后打球再也不会喝灰了,你阴雨天也可以训练了。老弟下次在县里打赢了,别忘了请我喝酒奥!”说着说着,他突然抱着肚子,倒吸了一口气,皱起了眉头,额头上顿时沁出了汗珠。望着他痛苦的表情,我的心一阵紧缩。我听说,队长最近身体不舒服,前不久才从地区医院检查回来。我说:“队长,你别干了,累了一天了,天这么晚了,赶快回家歇歇吧!”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很酸,队长因为穷,讨不到老婆,至今还是光棍汉一个,哪有什么家啊!他说:“不行!水泥凝固了,就不能压了”。“我去喊别人来干吧?”“不要喊了,明天队里还要上河工。”我拗不过他,只好给他提着马灯,他一边抹,一边和我聊天。我说:“队长,你也该成个家了,跟你差不多的人都小孩好几个了。有个老婆,晚上回去也有人给你烧碗热汤喝,天冷了还有人给你暖暖被窝”。队长听了半天没讲话。过了会他叹了一口气,说:“俺穷啊,哪有钱取老婆啊!这辈子就这样过了。”接着又说:“老弟,你看我现在不也挺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聊着聊着,又聊到了篮球,他又向我询问有关篮球方面的问题。说到开心处,还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夜,已经很深了,雨也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当队长抹完最后一下时,累的已经站不起来了。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长长的舒了口气,在口袋里摸了半天,拿出一块皱巴巴的小纸片,然后又从裤腰带的烟荷包里捏了一撮烟叶,用舌头在纸上舔了舔,卷起来一支手指粗的烟卷,点了火,深深地猛吸了几口,高兴地说:“哈哈,这回鸟换炮了,等过些日子,我从河工回来,一定跟老弟比个高低,谁输了谁给一包‘前门’!”说完他还硬是跟我勾了手指。这时的他,憨厚的脸上,笑得像个孩子,很甜,很美……
夜,依然是那么黑,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寒夜显得更深、更静。我目送着队长提着马灯,在夜幕中逐渐消失的那疲惫不堪的身影,心情格外沉重,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
一个多月后,球场投入使用。第一场球就是学校邀请生产队的比赛。我在这群刚从河工回来的农民球友中寻觅,已不见队长昔日矫健熟悉的身影。他的队友们告诉我:队长走了。前些时在徐州医院检查,说他肝上长了个疙瘩,医生叫他住院手术治疗,他没住,自恃身体好,没当回事。队长争强好胜,带领生产队的老少爷们,在河工与邻近生产队“杠”上了,每天都要争个高下。为了争先进,夺红旗,赶进度,抢工期命都不要了,硬是给累垮了!河工上最累最危险的就是推独轮车,在河底装上满满的一车淤泥,前面的两个人弓着腰拉着绳子,后面一个人掌着车把推。推车的人既要用力从河底往上推,还要掌好把控制方向。每一趟都是铆足劲,一鼓作气跑着到堰顶,如果中间“断气”了,力接不上,车子就可能倒退下去,甚至翻车,推车人很危险。队长自恃是“力士”,抱着车把不放,有时他只安排一个人给他拉车,把别的车配上两个人。终于有一天倒在了河堤上,再也没能起来……“队长临走的时候给我们说:“俺说好的扒河回去和学校打场球,看来打不成了。等俺病好了,再和学校决个胜负,你们叫陈老师把'前门'给俺准备好……”听着社员们七嘴八舌地叙说,我的心里非常难过。七十年代医学不发达,医学知识也没有今天普及,队长不识字,只知道肝上长了个疙瘩,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仿佛看到了在红旗猎猎、人声鼎沸、热火朝天的工地上,队长赤膊上阵,推着装满淤泥的独轮车,在抓牢车把起步的那一刻,车绊深深地嵌在他两肩的肌肉里的影像定格和他喊着号子,竭力冲向堤顶的飒爽英姿!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队长手提马灯抹压球场和我打赌的身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队长没能在自己亲手修建的场地上打一场球,我们还没有比个高低,却带着遗憾,永远离开了我们。这场球,家心情都非常沉重,球场上没有昔日肆无忌惮地狂呼乱叫,再也听不到队长那声若铜钟的叫骂声。
队长走了,队长的精神在发扬光。举步维艰的农民体育,经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已得到了长足发展。今天每个行政村都建有“体育文化广场”,有标准的水泥球场以及配套的健身设施,农民有了自己的体育休闲场所。队长所在的镇,86年被评为江苏首批体育先进乡,在第二届全国农运会开幕式上受到体委表彰。队长的队友们曾蝉联三届徐州市农民篮球赛冠军,并代表徐州市参加了江苏第二届农运会。每次赛,队友们都力争赛出好成绩,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老队长;庆功宴上,也忘不了给队长添杯加盏。新学年伊始,我总要向新队员介绍这片水泥球场的来历,讲述那过去的故事……
光阴荏苒,几十年过去了,我也早已调离了这所学校,但当年队长提着马灯抹压球场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在全国第十三个全民健身日来临之际,我写此文,以追念我昔日的农民球友。他的那一盏马灯,将永远照亮我前进的道路。
作者简介:陈桂祥,男,中学高级教师(已退休)。曾三次带队参加全国中运会、会、农运会。1986年被徐州市授予“群众体育训练先进工作者”,2002年被江苏教育授予“优秀教练员荣誉称号”。
免责声明: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标签: